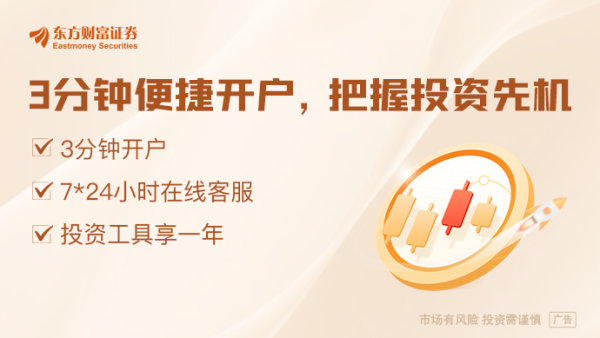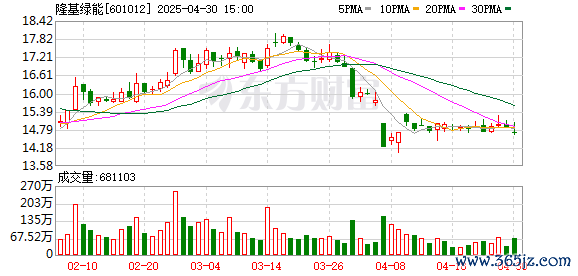在这纷扰尘世之间,光阴如流水般悄然滑过,三十余年如梦初醒。往昔的银幕上,有一部影片犹如惊雷般震撼了大地,它的名字叫做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。那是一股从遥远东欧吹来的英雄旋风,犹如一场无声的战鼓敲响了我们年轻的心扉。彼时,除了那些家喻户晓的杨子荣、严伟才之外全国有多少个证券公司,我的记忆深处还藏着一位永不屈服的侦察英雄,名曰“瓦尔特”。
时光倒流至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求学之时,瓦尔特这位银幕英雄竟亲临上海。那一天,文艺会堂座无虚席,而我,只是芸芸众生中一个踮起脚尖、远远眺望偶像的普通青年。座谈会上,我怀着一丝大胆的冲动,从服务员手中接过了瓦尔特的水瓶,试图为他添上一杯茶,却招致一位小官僚的冷眼相待。活动末尾,我心怀激动,想用自己省吃俭用买来的傻瓜相机为这位英雄留影,却被那些狐假虎威的接待人员无情推开,嘲讽着我的鲁莽。那一刻,我只得目送瓦尔特高大身影远去,心中既敬且怜。
岁月如指尖流沙,转眼二十多年后,我以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踏上了塞尔维亚这片土地。瓦尔特曾浴血奋战的萨拉热窝已成为历史,贝尔格莱德却依旧是这片土地上的心脏。我执念于寻找那个心中的英雄,哪怕名字早已不再“瓦尔特”,而是巴塔·日奥伊诺维奇,我仍固执地称呼他为瓦尔特。
展开剩余67%抵达的第二日,消息传来——瓦尔特将与我们见面。午后的阳光洒落在贝尔格莱德的古老街巷,迷人却无法驱散我内心的激动。那日的脚步如飞,心跳如鼓,我奔赴塞尔维亚影协,准备朝圣那位反法西斯的勇士。踏进那被北约轰炸洗礼过的哥特式古楼,沿着泛黄的木质楼梯攀上,等待那熟悉的铿锵脚步。
他来了——昔日叱咤风云的青年已成鬓发稀疏的老人。眼神中藏着慈祥与孤独,却难觅昔日的机警与锋芒。是他吗?是那个深植我心三十余年的战士吗?是,却又仿佛不再是。无言以对,我猛然迈步向前,像久别重逢的儿子,张开双臂拥抱了这位老人。泪水滑落,我哭,他亦哭,同行的导演演员们也泣不成声。
那一天,我们的谈话多次被他的手机铃声打断,而那旋律正是《保卫萨拉热窝》的主题曲。尽管他总是去掐断铃声,我却希望它自由响起,那熟悉的旋律仿佛穿越时光,诉说着无言的情怀。老人虽是功勋演员,却失去了当年祖国的荣光——那个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割裂与分裂。那些曾经沐浴社会主义阳光的艺术家们一夜间失去一切,连曾经的荣耀也如风中残烛。他无奈道:“我们的国家不存在了,党不存在了,电影的辉煌也不复存在,只有‘瓦尔特’的旋律永存我们心中。唯独中国人民没有遗忘我们,我羡慕你们的幸福。”
那一刻,情感如潮水般涌动,离别之际我再度拥抱他,却不敢直视那双布满沧桑的眼睛,仿佛见到了家乡老父亲目送归城时那不舍的眼神。往事如烟,思绪纷飞。我想起多年以前在上海为他倒水的场景,感慨自己竟然如此幸运,能与心中英雄如此接近,却也涌上一丝淡淡的忧伤——此别或许一生难再相见。
次日,和电影人同行,途经一座桥下,见几位老人摆摊,其中一位白发老人卖着一架苏联产的老式手风琴。经过讨价还价,我们以相当五百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它。老人深情一问:“我还能再拉一遍吗?”那一刻,熟悉的旋律从指尖流淌,仿佛岁月的洪流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光辉的时代。我们无法探究老人过往,却能感受到他曾在舞台与录音棚中的辉煌。可为生计所迫,这琴成为他无奈的出路。我心生不忍,欲多付些许,却被婉拒,他说:“带给中国同志,我心欢喜。”那琴的归宿,恰是我这美好时代的见证。
岁月无情,历史纷乱,但英雄的光辉永不磨灭。愿我们铭记那些浴血奋战的灵魂,坚守正义与信念。愿光明与和平长存人间,愿我们在纷扰中不失初心,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。
发布于:山西省捷希源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